读书节系列 | 母亲的读书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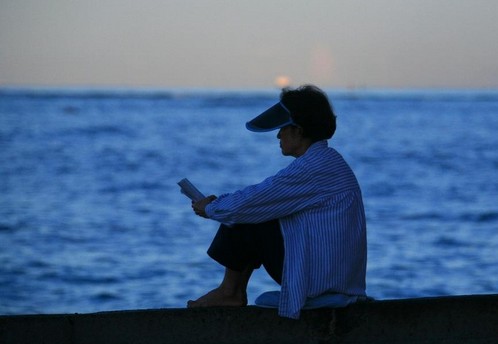
学校一年一度的读书节又开始了。
听一个资料说,我们周边有些国家,平均每人每年读四十多本书,我们国家平均每年四个人读一本书。我不知道这组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也不知道一本五千字的《道德经》和一本500页的卡通书是不是都算一本书,更不知道这组数据是不是有妄自菲薄的嫌疑,至少我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一半有不有?我还不自信。
读书需要时间,更需要心境,像这几天的天气,整天微雨蒙蒙,云遮雾罩的,思绪都潮湿了,氤氲开去了,哪怕偶尔拿起一本书,一行行文字流水一般从眼前掠过,却没有留下痕迹来。
于是,与其拿着一本书发呆,不如将书随便往哪儿一扔,闭目养神。
一闭目,我眼前却浮现出一些往事来,和读书有关的,和母亲有关的。
父母工作的时候,从来就是聚少离多;退休之后,终于生活在一起了,整天。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二老就常常拌嘴,哪怕是打个纸牌,都会争。争归争,日子照样过着,谁也离不开谁。夫妻没有隔夜仇,说的也许就是这种情况。
一拌嘴,母亲每每就会拿“读书”说事,说:
“你就会在我面前摆格,欺负我没过读书,你个剥削阶级!”
“好男不跟女斗,我懒得和你争,没读书哩,有什么办法?”父亲转身走了。
说我父亲是“剥削阶级”,事出有因,父亲成分高,富农,富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是属于团结和限制的一列,这个命运的标签甚至殃及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那时,每次开学填成分一栏是让我最揪心的,总是要等到没有人的时候才像小偷似的在“成分”一栏写上“富农”两个字,总是尽量把这两个讨厌的字写得又轻又小,不像那些“贫农”同学,写得又粗又大,连字格子都装不下。我妈妈出身“雇农”,却不能填,成分是随父亲的,宿命。
父亲长母亲8岁,在民国湖南省立三中读过高中,尽管在求学的过程中,经历过很多周折:大冬天,穿着半截裤子走十多里山路去别乡求学;读高中时,还要肩扛一根杉树扁担,一头挂着几只鸭,一头捆着一袋米,走上一整天才能赶到县城的学校——鸭米是用来换取学费的。平心而论,比起母亲来,父亲还是幸运多了,毕竟还是读出来了,在那时工农干部成堆的机关,“高中生”可是凤毛麟角,尽管“富农”这块标签给父亲带来了许多苦涩。
母亲1937年8月出生在衡阳西渡的一个叫上桥的小山村。
适逢抗战爆发,抗战之初,中国军队虽浴血奋战,却难敌日寇的铁蹄剑锋,大片河山相继沦丧。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湖南经历了最著名的三大保卫战,长沙保卫战、衡阳保卫战、常德保卫战。母亲对衡阳战事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外婆挑着箩筐随着绵延不绝的村民飞也似的逃难的情景:躲日本。
听母亲说,她5岁时,由我外婆领着去拜了孔夫子,然后和一位老先生念过几天《三字经》。这是我母亲的全部读书生涯,——这还得益于湖南民间的一种信仰:没有拜过孔夫子,没有念过《三字经》,来世会变猪变狗。
母亲4岁的时候,我亲外公死了,在战乱的颠沛流离中,我外婆带着母亲改嫁了,外公是在湘江河里跑船的,那时母亲7岁。在母亲的叙述中,外公对她不好,因为我外婆一过门,我母亲就被外公给别人(我外公的姐姐,按理应叫姑姑)做了童养媳。母亲名义上的老公12岁光景,经常无端打她,有一次还将母亲推到了河里,差点淹死。在母亲看来,如果我亲外公在,她就不会吃这么大的苦,还会有书读,因为我亲外公是识文断字的,那时在衡阳开的一家印刷厂当工人,家里藏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工厂主是村里的一个大户人家,和我亲外公也许还有点远亲。
母亲说起这个说了一万遍的故事,有时会得到父亲不冷不热的一句话:
“你就是穷得好!不然你有干部当?那个时候,工农干部当家,哪像现在?”
于是一场争吵就难避免。我们知道,父亲心里有怨气,自己一个高中生,因为成分高,虽然作风正派,能力过人,工作勤勉,但直到退休,尽管混了个正科级,却没有堂堂正正地做过单位的一把手——哪怕是单位没有一把手,父亲主持工作,他的头衔上也要带个“副”字——心里憋屈。父亲是个心高气傲的人,母亲一语中的:
“你就是骄傲!你比哪个还强,比县委书记还强!”
“县委书记当不下呀?走了这么多单位,哪个比我强呀!”父亲不服。
虽然吵架,但母亲人前人后都为父亲自豪——
“我老倌子不错呢,是个老高中生哩!”
“我那个老倌子,家务事一点不晓得做,但文章写得好哩。”
回过头来看,父亲说母亲“穷得好”也不是没有道理——
1953年,县里有干部来“耒阳水上运输公司”开会,闲聊时,说公司还缺一个团委干事,要个女的。有人推荐了母亲,那时她16岁,在我外公船上帮工好几年了。干部让人找来看看,一看,样子还机灵,便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要母亲写“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几个字让他瞧瞧。母亲不会写“党”,那时是写繁体字,她只写了上半截,下面的四点水不会写。干部笑过一阵之后了,当场拍板到让母亲来当这个团干。这是母亲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从此走上工作岗位。
“哎呀,那个干部好!好负责!”几十年之后,说起那个干部,母亲总是赞不绝口。
那干部每天要母亲写两百字,上午布置,下午检查。
“写什么呢?”母亲问。
“就抄‘团的基础知识’吧。”干部丢给母亲一本说,说。
如果出差,干部就吩咐别人督促。后来那干部调走了,母亲也换了不少单位,学字却一直没有落下。当干部了,自尊心强了,看公文,遇到不认得的字就写在手掌上,不会读音,就问别人,问了之后,就在旁边写一个同音字(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音字),随时随地地记。
有一次我还作为法官判了我父母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关于“简陋”的“陋”的读音。我说出字音后,父亲乐了:
“你看啦,是不是读‘漏’啦?‘简丙简丙’,还‘煎饼’哦!”
说得我们大笑不已,母亲更是笑出了泪来:“哦荷,那个老刘讲是读‘丙’啦!”
“煎饼”是有典故的——
我读初中的时候,母亲学做“煎饼”。她不知道先将搅拌好的米糊放进一个平底勺里匀好之后,要在烧沸的油锅里煎得半熟才让它浸在油里面,而是直接把平底勺往油里一放,于是米糊整个儿在锅里便爆成了一朵花。
这个典故让父亲笑了好几十年。好的,别说这个典故了,单说这个词。
“简陋”,算个生僻词,对母亲来说,能知道就真的不简单了。
我做父亲后,母亲曾帮着我带孩子。那时我在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教书,案头有一本中专生用的小册子《三千常用字》,母亲饶有兴趣地读里面的字给我听,让我正音,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知道其间大部分字的读音,词意也知道不少。
如果不知道实情,我都不敢相信母亲只是一个读过几天《三字经》的人。
有时,来了兴致,母亲还会让我告诉她某个字为什么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我心情好的时候,也会给母亲说说最简单的“六书”:
“人靠在木头上搞什么?”
“歇息咯。”
“你看,这就是‘休’字。”
“哦呵,真的啦,哪这样有意思?”
别人家的孩子有钱或做官,母亲不羡慕;要是哪个家的孩子读了一个什么好学校,母亲就羡慕得不得了,甚至还夹杂着些许眼红的成分。有时母亲也会对人说“我四个孩子不错呢,有研究生大学生中专生”,让我都觉得难堪。我专科毕业后,脱产进修弄了个本科,后来又混了个在职硕士,其他三个也只是通过自学或函授获得文凭的杂牌军,名副其实的“武大毕业生”:函大、夜大、职大、电大、自考。
母亲对读书人确实有些偏心。20多年前,我开始抽烟,那时弟弟也二十好几了,也学着抽烟了。母亲让弟弟不要抽,抽烟不好,花钱不说,还伤身体,一堆的苦口婆心。
“哥哥也吃烟啦!”弟弟不耐烦,顶了一句。
“你哥哥是知识分子,要动脑筋啦,你又不是知识分子,不要动脑经。”妈妈说。
一句话,憋得我弟弟无言以对。——年前,我把它当成逸事说给几位茶友听,听得他们个个前仰后合。其实,如果当初我母亲反对我抽烟,现在也许就不会因为这个不良嗜好而招人嫌恶了,对吧?
退休后,母亲迷上了保健,常常被来推销保健品的人弄得晕晕乎乎的。这些人除了给老人家发些香皂杯子这些小恩小惠外,总会召集老人家们去听讲座,然后发好些花花绿绿的宣传册,推介各式产品,药物的,器械的,说明书里面甚至还有整版的英文,拉虎皮,作大旗。父亲学过几天英语,知道几个句子,也就“longlongago”、“goodluck”之类,平时也常在母亲面前经意或不经意地“摆格”几下。
母亲萌发学英语的念头,是不是和这些有关,我不知道,但母亲确实开始“学英语”了。
一次回家,母亲让我写好26个字母,还要用汉字注好音,一遍一遍地教她读。再次回家,母亲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会26个字母了,一边默写,一边读给我听;从父亲那里依样画葫芦学来的几个单词诸如“book”、“desk”等也一并念给我听。发音是有点滑稽,但那认真劲儿,丝毫不逊色于一个专心致志的小学生。我暗自笑了。我想,如果母亲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一定能成为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的。
这些年,让母亲最为开心的莫过于我大外甥女了。她在四川大学本硕连读后,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博士,还在这里收获了爱情,丈夫博士后毕业留在中科院工作。四年前,父亲80大寿的时候,外甥女从北京寄来了一些钱和一封信。
信封上那明晃晃红灿灿的“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几个字,成了单位的一桩不大不小的新闻,一个小县城,能到北京工作的还真的不多见哩。一起跳广场舞的老人们见到母亲就夸赞,让我妈妈喜不自禁。
母亲说,我们家三代人,一代比一代强,以后呀,还要出一个“博士后后”。
我们说没有“博士后后”。母亲说,管他,反正比“博士后”还要强!
母亲的读书梦在晚辈们身上圆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她高兴的呢?
2014-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