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无聊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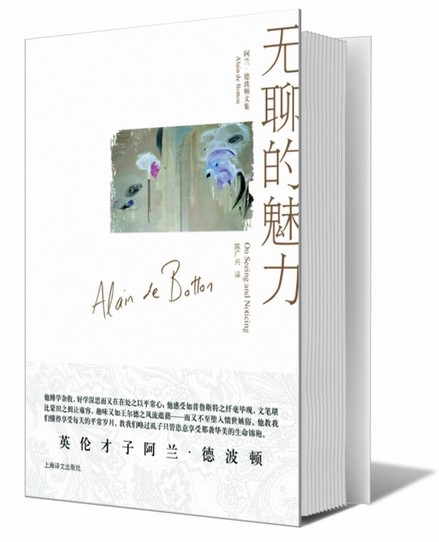
追逐新鲜事物的本能
英国哲学家阿兰·德波顿说:“互联网的问题是,它帮我们阻挡了无聊以及它的许多好处。”我们的时代面临的一个挑战是重新学习如何集中注意力,而注意力跟我们对无聊的忍受度有关。我们的心灵像我们的身体一样,需要时而无聊一下,以便我们重新学习专注。
过去10多年间,网络对我们的专注力造成了极大冲击。我们已经不可能长时间静静地坐着思考了,总是忍不住去查看一下电脑或手机。德波顿说:“问题部分在于我们对新鲜事物的痴迷。我们的本能令我们不断地沉迷于当前事物,觉得某个时候,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会发生一件横扫旧的确定性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立刻得知这件事,就无法理解自己或者我们的同胞。我们还要不停地去发现新的文化作品,并且同时不让任何一件作品成为我们心灵的负担。”
美国社会批评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在《纽约客》上撰文说:“在网络时代,许多人对自己的无聊浑然无觉,因为这种无聊披着现时、新颖的伪装。一个人要发觉自己很无聊,他需要辨别不同的时刻。如果一个人只生活在现在,就很容易错误地以为新鲜事物不断入侵是跟以前的一切彻底决裂。”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也曾描述过这种情形:“从前,在对历史没有意识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开始,也没有什么东西终结。今天,一切刚开始时就终结了,刚出现就消失了。但一切又都重复自己,再次开始。对它的兴趣越来越弱,所以新闻变得更极端、更集中,到最后越来越快地耗尽。人们熟知的现象,饱和、无聊、从感兴趣变得厌倦,产生了一些致力于克服这些反应的技术,呈现技术,各种呈现新闻的技术。我们有假新闻,通过戏剧化虚构假的新鲜事物。”
马尔科姆·麦卡洛在《周围的常见事物:形体化信息时代的注意力》一书中说:“更安静的生活需要我们更多地留意世界,更多地把技术用于满足好奇心而不是用于征服。它在直接的感受中寻找安慰和休息,它看重持久性,而不只是新鲜感。它拉伸、延展现时,超越最新的推特,超越下一年财政季度,直到感觉超出了你的人生。”
德波顿在《无聊的魅力》一文中说,资产阶级的生活很无聊,但拥有审慎的魅力,我们应该学会欣赏这种无聊生活的魅力:“在17世纪荷兰画家霍赫的画作中,小资意味着穿着简单而又漂亮,既不粗俗也不做作,跟孩子的关系很自然,色而不淫。它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在霍赫700年前,蒙田写道:‘发起破坏、控制一位大使、统治一个国家是很光辉的行为。指责、发笑、买卖、爱恨、跟家人一起平静地生活,既不怠惰又不辜负自己,做到这些更了不起、更罕见、更困难。’”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有着不同反应,有人感到兴奋,而有人感到无聊。为什么青少年在看莎士比亚戏剧时会感到极其无聊?为什么有人在博物馆感到无聊,而有人看得津津有味?关键是要把外界事物跟内心的兴趣结合起来。这就是老师的任务,他们可以指出为什么一个看上去很遥远的东西其实跟你最关心的事情有关。变得成熟就是变得对越来越多的事物越来越感兴趣,因为它们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美国漫画家司各特·亚当斯说:“专家们说,我们的大脑需要无聊,以便我们处理思想,保持创造力。我认为他们说得对。”他用他的亲身经历来证明这一点,他总结说,他最好的创意都是在外界没有惊扰、娱乐时冒出来的,他的创造力源自他无聊的童年。“我成长于一个很小的山区小镇,我的童年过得没有一点意外。我们家的电视机只能收到一个台,我们习惯了图像不停地跳动。我们也没有什么玩具。什么也不做的时候,我会盯着窗外的冻土带,看着小鸟在飞行途中冻死。夏天,我每天都会骑几小时的自行车,想象一个冰淇淋免费、农场的狗不会咬自行车的孩子的世界。我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假装很认真,同时在脑子里编代码。我还想象我发明了一条腰带,可以使我像鸟儿一样飞翔。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失望地发现,我还是要穿上裤子步行。”
现在,亚当斯开始担心他得不到足够多的无聊:看电视时看到广告可以快进。在商店里排队时可以查邮件,或者玩《愤怒的小鸟》。跑步时可以听音乐、看电视上的新闻标题。他说:“假如世界上的领导人和创新者都不再无聊、创造力下降,人们将变得更加教条。如果你不需要去创造性地思考,最容易走的路线就是采取你的政党、宗教和文化默认的立场。你会看到更多衍生剧和电影续集。”
但有些心理学家认为,不要拔高无聊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无聊只是大脑在告诉你,你应该做点别的事情。但是大脑不是一直知道最合适的选择。如果无聊的时候,你把精力用于弹吉他或烹饪,你会快乐起来。但如果你去看电视,那只会让你在短期内感到快乐。如果你的小孩感到无聊,你把iPad给他,他可能就不再感到无聊,但是他没有学会自己找开心,或者自我控制。而自我控制是能够从一个情境向下一个情境延续的。小孩不仅学习自己找开心,而且在其他领域也将更能控制自己。
极端的无聊
无聊不单是一种个人体验,还被认为具有政治意义。1924年,德国社会学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论无聊》一文中说:“大部分人没有多少休闲时间,他们把所有的精力用于获取生活必需品。但没有哪个人一点休闲时间也没有。办公室不是一个永久的庇护所,过周末是一项制度。因此,从原则上说,在那些美丽的自由时光,人人都将有机会陷入真正的无聊。”“但人们可以去看电影,图像开始接连出现,人们在观看过程中忘记了自己,巨大的黑洞上闪动着不属于任何人但论尽所有人的虚幻的生活。谁能抵挡住那些精致的耳机的诱惑?听广播不会带来有教养的对话,只会让人变成全世界噪音的操场,不让人有一丝无聊的权利。人们沉默、毫无生气地坐在一起,就像他们的灵魂飘到了远方。但那些灵魂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在飘荡,而是被狗一样的新闻纠缠着,很快就分不清谁是猎人、谁在被捕猎。哪怕是在咖啡馆里,当你想着像豪猪一样卷成球时,威风凛凛的喇叭将抹去一切个人存在的痕迹。”
克拉考尔说,如果你不想被世事驱逐,唯一能做的就是无聊着,因为它能保证你掌握自己的存在。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到过无聊,你就没有存在过,只是无聊的又一个对象,飘在屋顶上,或者像胶片一样被卷起。如果你真的存在着,你就别无选择,只能因为无所不在的喧嚷而感到无聊。在星期天的下午,当所有人都出去了,你最好在火车站游荡,或者更佳的做法是,待在家里,拉上窗帘,悲伤地坐在沙发上向无聊屈服,任一些想法浮现在脑海中,假装很认真地考虑各种方案。最后,满足于无所事事——同情桌上不会跳的琉璃蚂蚱,因为它是琉璃做的,同情傻乎乎的没有任何念头的仙人掌。你跟这些装饰品一样,内心骚动但没有任何目标,渴望被放在一边。但是,如果你耐心的话,你就会体验到天堂般的幸福。你的灵魂在膨胀,你感到充满激情。这股激情覆盖了你、他人和全世界,接着无聊就会消失。
美国社会批评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说:“1968年一代人一个流行的口号是无聊是反革命,克拉考尔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在他看来,极端的无聊不是消极被动接受的借口。它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世界,对我们的困境给出不同的解释,甚至使我们敢于去憧憬不同的未来。”无聊和消遣并非相互对立的事物。克拉考尔既喜欢极端的无聊,也不鄙视现代技术和喜欢跳舞、旅行、看电影的大众。相反,他认为这些转移注意力的活动可以使人们避免成为过剩的技术的帮凶。克拉考尔写过一篇著名的随笔,歌颂电影令人分心的潜力,但他关于旅行和舞蹈的随笔指出,我们需要创造多样化的体验。他认为,旅行和舞蹈能够暂时中止现代生活的理性化过程:“旅行和舞蹈能把人们从世俗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使人们能够从劳作中获得审美体验,超越短暂、偶然的东西,体验到永恒和绝对。在旅行时,去哪儿变得不再重要,人们摆脱了束缚,想象无限在自己面前展开。在火车上,他们已经到了另一端,他们站在一个新世界中。舞者在旋律中把握到永恒:他旋转时的时间和打败他的时间之间的区别是,他在一个非本真的地方感觉到真实的快乐。”极端的无聊和极端的消遣都能使我们更接近这种真实的快乐。它们都值得歌颂,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平庸、中等的无聊和消遣。

